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公文有哪些文體文體學(xué)的定義
邁克爾·舒德森將新聞視為一種文化形式,關(guān)注其歷史生成的過程,主張將新聞業(yè)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并引入有關(guān)權(quán)力、文化的理論,應(yīng)用社會(huì)科學(xué)的概念與框架進(jìn)行分析
的定義.jpg)
邁克爾·舒德森將新聞視為一種文化形式,關(guān)注其歷史生成的過程,主張將新聞業(yè)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并引入有關(guān)權(quán)力、文化的理論,應(yīng)用社會(huì)科學(xué)的概念與框架進(jìn)行分析。
寫作本文,旨在回應(yīng)國內(nèi)有關(guān)新聞史研究路徑的討論文體學(xué)的定義。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國內(nèi)新聞學(xué)界就開始了對中國新聞史研究路徑的反思(寧樹藩,1982)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相關(guān)討論更趨熱烈,2007年到2010年間,《新聞大學(xué)》與《國際新聞界》先后開辟專欄,新聞史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名家紛紛撰文,就新聞史研究展開全方位的探討。研讀相關(guān)文獻(xiàn),主要成果如下:一是強(qiáng)調(diào)研究者應(yīng)樹立“本體意識”,確立新聞業(yè)自身在新聞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書寫“報(bào)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bào)刊”(寧樹藩,2007;郭麗華、寧樹藩,2007;黃旦,2007;吳文虎,2007);二是主張研究者應(yīng)具備“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擺脫“編年史”的思維定式,尋找史料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從而使新聞史獲得鮮活的生命力(李金銓,2009;黃旦、瞿軼羿,2010;王潤澤,2010);三是探討新聞史研究范式轉(zhuǎn)型的可能路徑,提出從傳播學(xué)的5W 框架、媒介生態(tài)學(xué)、主流史學(xué)文體學(xué)的定義、社會(huì)史范式、社會(huì)建構(gòu)論中獲得新的視野,進(jìn)行更為專業(yè)化的研究,實(shí)現(xiàn)路徑更新(田秋生,2006;李彬,2007;吳廷俊、陽海洪,2007;王潤澤,2008;裴曉軍、路鵬程,2008;唐海江,2010)。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討論已全面地涉及了新聞史研究的各個(gè)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然而,在完成了面上的掃描后,著眼于個(gè)案和點(diǎn)的考察尤顯重要,邁克爾·舒德森(下文簡稱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正是這樣一個(gè)值得深入探討的經(jīng)典個(gè)案。
眾所周知,舒德森乃新聞史研究名家,其研究獨(dú)樹一幟,有著廣泛的影響公文有哪些文體。在其名著《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中譯本(舒德森,2009)封底有一段這樣的推介語:“作者跳出傳統(tǒng)新聞史研究囿于描述性或闡釋性的窠臼,開創(chuàng)了美國新聞史研究的社會(huì)科學(xué)流派。”在另一本名著《新聞社會(huì)學(xué)》中譯本(舒德森,2010a)的譯者后記中,譯者徐桂權(quán)作出了這樣的評價(jià):“他的論著的鮮明風(fēng)格是兼具歷史經(jīng)驗(yàn)與思辨分析,史論結(jié)合,論從史出,并且總是在社會(huì)語境中觀照媒介,將新聞的生產(chǎn)與社會(huì)的變遷聯(lián)系起來。這樣一種研究取向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可見,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所具有的方價(jià)值得到了上述譯者的高度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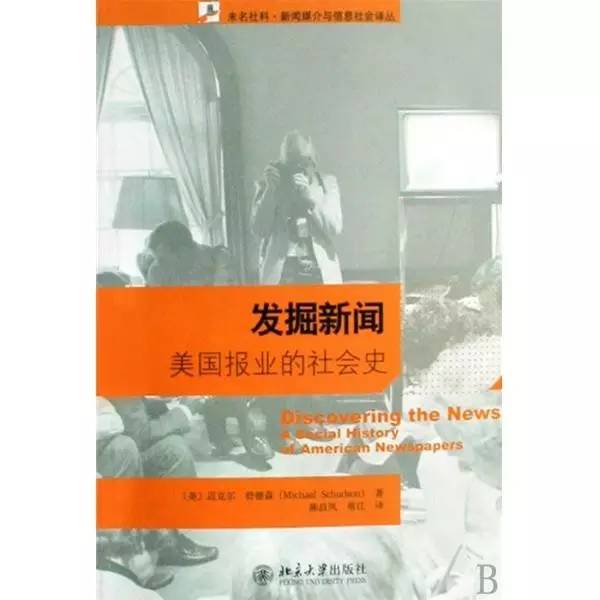
查閱文獻(xiàn),國內(nèi)涉及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主要成果如下:迄今為止,最有價(jià)值的研究文獻(xiàn)為《從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談》(陳昌鳳,2003),作者依據(jù)文獻(xiàn),對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進(jìn)行了述評,并將舒德森(該文稱為“夏德森”)作為新聞史研究傳播學(xué)派的代表進(jìn)行了個(gè)案考察,發(fā)現(xiàn)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呈現(xiàn)出社會(huì)學(xué)視角,在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上均突破傳統(tǒng),但在該文中,舒德森僅是美國新聞史研究演進(jìn)過程中的一環(huán),作者的分析主要依據(jù)舒德森的博士論文《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抓住“兩個(gè)模式”展開分析,尚未充分地展開;張彥(2009)針對埃默里的《美國新聞史:大眾媒介解釋史》與舒德森的《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展開比較分析,探討兩書在歷史敘述上的差異。此外,馮悅(2010)研究了美國新聞史教研的問題與趨勢,文章提及舒德森對美國新聞史研究所提出的批評,并將其研究歸入“文化史”方向。綜上,既有的研究成果雖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啟示,但由于受到研究素材的局限,在廣度與深度上有待進(jìn)一步開掘。鑒于此,本文嘗試依據(jù)中外文獻(xiàn),首先從理念與實(shí)踐兩個(gè)層面探討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特征,隨后分析其背后的學(xué)理脈絡(luò);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發(fā)掘其方價(jià)值,以期回應(yīng)學(xué)界近年來的相關(guān)討論文體學(xué)的定義。
舒德森最有影響的新聞史研究成果無疑是研究新聞客觀性的《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其他主要研究成果則收集在《新聞的力量》(舒德森,2011)和《為什么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舒德森,2010b)兩本論文集中公文有哪些文體。1995年出版的《新聞的力量》一書分上中下三部,起首上部名為“歷史視野下的新聞”,收集了4篇新聞史研究論文;2008年出版的《為什么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則收集了兩篇新聞史研究論文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另外,還有一篇延續(xù)其博士論文話題的重要論文《美國新聞業(yè)中的客觀性準(zhǔn)則》(Schudson,2001)則發(fā)表于2001年8月號的《新聞學(xué)》,尚未譯成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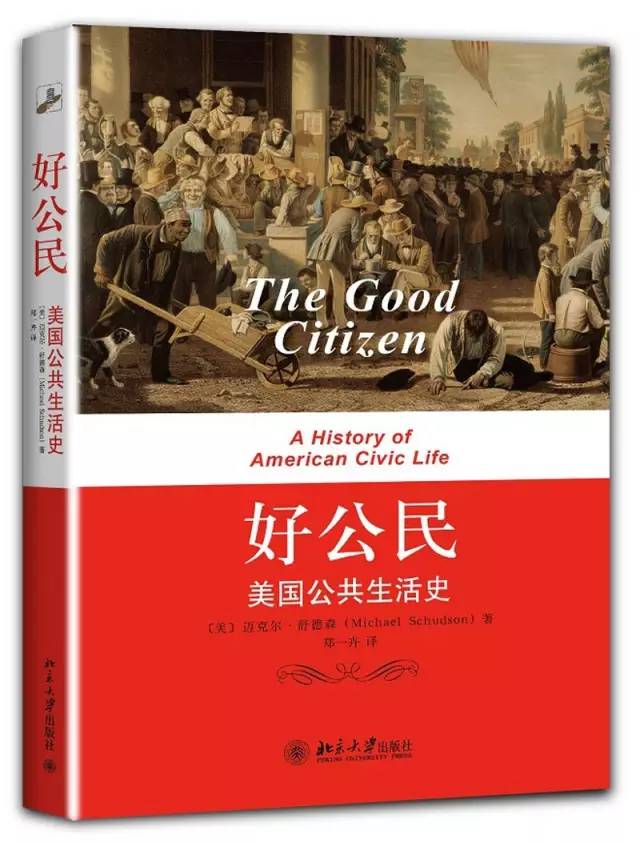
在從事新聞史研究實(shí)踐的同時(shí),舒德森也積極參與美國新聞史學(xué)界有關(guān)新聞史研究路徑的討論,并提出了系統(tǒng)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87年發(fā)表于《大眾傳播批判研究》的論文《史學(xué)?》(Schudson,1987)、1991年收集于《大眾傳播質(zhì)化研究手冊》中的《傳播研究的歷史取徑》(Schudson,1991)、1997年發(fā)表于《新聞與大眾傳播研究季刊》的論文《新聞史研究的幾個(gè)棘手問題》(Schudson,1997)公文有哪些文體、2013年發(fā)表于《美國新聞學(xué)》中的論文《420或450年:作為文化形式的新聞與作為歷史形成范疇的新聞業(yè)》(Schudson,2013)。上述論著中,只有第三篇被譯成了中文,并發(fā)表在1998年第3期的《國際新聞界》。
新聞史研究什么? 這看似為一個(gè)不言自明的問題,新聞史自然是關(guān)于新聞和新聞業(yè)的歷史,然而,為何不同的新聞史家寫出的新聞史會(huì)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呢?原因在于對“新聞”“新聞業(yè)”的不同理解。
對于新聞和新聞業(yè),舒德森有著獨(dú)特的定義。在他看來,新聞是文化的一種形式,新聞業(yè)是一種歷史形成的范疇。作為文化形式的新聞,是人類社會(huì)特定歷史階段出現(xiàn)的一種文體,以特定的方式講述特定類型的故事,類似于小說、科學(xué)實(shí)驗(yàn)或是奏鳴曲,由某一個(gè)體或某個(gè)專門機(jī)構(gòu)依據(jù)特定的傳統(tǒng)與慣例生產(chǎn)出來(Schudson,2013)。
新聞和新聞業(yè)一體兩面,它們并非人類社會(huì)普遍和永恒的特征(舒德森,2011,p.35),有一個(gè)生成、發(fā)展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變化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不同的地區(qū)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如將新聞定義為刊載于定期出版物、報(bào)道新近事實(shí)、討論社會(huì)公共事務(wù)進(jìn)而形成公共的文體,那么,在西方,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新聞與新聞業(yè),萌芽于16世紀(jì),基本成型于18世紀(jì)。也即是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新聞與新聞業(yè)的存在時(shí)間不過400來年(Schudson,2013)。
既然新聞與新聞業(yè)是特定歷史階段生成的文化,并依時(shí)空而變,那么新聞史家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就是變遷。基于此,舒德森提出,新聞史的中心任務(wù)就是回答下列問題: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不同國家和地區(qū),新聞與新聞業(yè)如何演變? 呈現(xiàn)出何種不同面貌? 為什么? (Schudson,2013)
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式,新聞和新聞業(yè)產(chǎn)生、成長于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情境中,是人類實(shí)踐的產(chǎn)物。新聞和新聞業(yè)的變遷與社會(huì)的變遷密不可分,二者之間存在互動(dòng)關(guān)系,因而,舒德森強(qiáng)調(diào),考察新聞與新聞業(yè)的變遷,必須具備開放與互動(dòng)的視野,從媒介與社會(huì)互動(dòng)的關(guān)系入手,與其所處的社會(huì)文化情境的變遷相勾連。舒德森的這一思想,在《傳播研究的歷史取徑》(Schudson,1991)一文得以集中闡述文體學(xué)的定義。在該文中,舒德森指出,傳播史研究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宏觀史(macro-history),二是真歷史(history-proper),三是媒介機(jī)構(gòu)史(institutional-history)。宏觀史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傳媒技術(shù)的變遷如何推動(dòng)人類社會(huì)的進(jìn)步;媒介機(jī)構(gòu)史主要著眼于傳媒體系的歷史演進(jìn);有別于宏觀史和媒介機(jī)構(gòu)史,真歷史所考察的是媒介與文化、、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歷史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傳播的變遷與社會(huì)的變遷如何相互作用?”舒德森對于宏觀史與媒介機(jī)構(gòu)史提出了批評,認(rèn)為前者忽視了社會(huì)對媒介的影響,后者則很少考察傳媒對社會(huì)的影響,進(jìn)而明確地倡導(dǎo)真歷史。

對于新聞史研究,舒德森在強(qiáng)調(diào)問題意識的同時(shí),更重視理論的應(yīng)用,明確主張研究者應(yīng)具備理論自覺,引入社會(huì)科學(xué)的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那么,在具體的研究實(shí)踐中,應(yīng)該主要引入何種理論呢? 舒德森認(rèn)為,有關(guān)權(quán)力、文化的社會(huì)科學(xué)理論、有關(guān)權(quán)力與文化間相互關(guān)系的社會(huì)科學(xué)理論會(huì)有助于新聞學(xué)的研究(Schudson,1987)。為何是引入與權(quán)力、文化相關(guān)的社會(huì)科學(xué)理論作為分析工具? 舒德森的這一主張同樣是基于其對新聞與新聞業(yè)的定義。其一,既然新聞與新聞業(yè)是一種文化形式,應(yīng)用有關(guān)文化的理論進(jìn)行分析就是恰當(dāng)?shù)囊彩潜匦璧?其二,既然新聞與新聞業(yè)的發(fā)展變化與其所處的社會(huì)密不可分,受制于、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種社會(huì)力量,期間上演著各種社會(huì)力量的博弈,那么,應(yīng)用有關(guān)權(quán)力、權(quán)力與文化關(guān)系的理論進(jìn)行分析就是可能的也是合適的。
1982年,舒德森發(fā)表論文《敘事形式學(xué):報(bào)刊與電視上新聞報(bào)道慣例的出現(xiàn)》(Schudson,1982),該文研究了美國自1790年至20世紀(jì)初報(bào)刊有關(guān)總統(tǒng)國情咨文的報(bào)道在報(bào)道形式上的變化。論文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20世紀(jì)美國新聞界在進(jìn)行總統(tǒng)國情咨文報(bào)道時(shí)所普遍采用的一些慣例(包括概述式導(dǎo)語、倒金字塔結(jié)構(gòu)、以總統(tǒng)為主要角色、重視解釋等)是如何形成的?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舒德森發(fā)現(xiàn),自1790年至20世紀(jì)初,美國國情咨文的報(bào)道方式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完成了從速記式新聞到概述式導(dǎo)語新聞的轉(zhuǎn)變,確立了新的慣例。(Schudson,1982)舒德森不僅描述了這一變化的過程,并從媒介變遷與社會(huì)變遷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入手,在解釋報(bào)道慣例變遷的原因的同時(shí),分析其對社會(huì)生活的影響。在分析原因時(shí),舒德森并未將其僅僅歸結(jié)于傳播技術(shù)的變遷(電報(bào)的應(yīng)用),而是更加重視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社會(huì)因素,包括美國現(xiàn)實(shí)的變化、新聞工作者職業(yè)意識的覺醒與自主性的增強(qiáng)、報(bào)紙讀者結(jié)構(gòu)的改變等。在分析影響時(shí),他深刻地指出,這些慣例強(qiáng)化了關(guān)于世界的某些解釋,以致使報(bào)道本身成為敘述形式的中的一部分(舒德森,2011,p.59)。
1994年,舒德森發(fā)表力作《發(fā)問權(quán)威:美國新聞采訪史,1860年代至1930年代》(Schudson,1994)。該文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新聞采訪作為一種社會(huì)實(shí)踐和寫作形式,在美國新聞史上是如何制度化的? 該文描述和分析了采訪作為一種社會(huì)交往方式及新聞職業(yè)中的一個(gè)核心部分,在美國歷史上產(chǎn)生公文有哪些文體、受到質(zhì)疑并最終被接受和制度化的歷程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舒德森認(rèn)為,作為制度和慣例的新聞采訪具有現(xiàn)代性與美國性,也即是說,具有特定的時(shí)空背景。同時(shí),新聞采訪的興起本身也促進(jìn)了文化與社會(huì)的現(xiàn)代性。換句話說,采訪的興起與制度化有賴于美國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同時(shí),其本身也是美國現(xiàn)代化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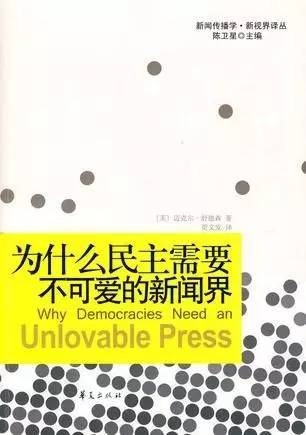
2001年,舒德森發(fā)表論文《美國新聞業(yè)中的客觀性準(zhǔn)則》(Schudson,2001),對其博士論文所涉及的客觀性話題進(jìn)行了更為充分的探討。論文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為什么美國新聞業(yè)中產(chǎn)生了客觀性這一職業(yè)準(zhǔn)則? 舒德森從普遍的社會(huì)現(xiàn)象的視角,應(yīng)用涂爾干和韋伯的社會(huì)學(xué)理論,聯(lián)系美國的歷史,對作為觀念和新的文化形式的客觀性展開考察,指認(rèn)了催生道德準(zhǔn)則的四個(gè)社會(huì)條件,發(fā)現(xiàn)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的美國恰好同時(shí)具備了這些條件,為滿足內(nèi)部社會(huì)整合與社會(huì)控制的需要,新聞界提出了作為職業(yè)意識形態(tài)和職業(yè)操作守則的客觀性準(zhǔn)則。
至此可以對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取徑做一個(gè)總結(jié):其一,舒德森主張研究新聞史要從問題開始,關(guān)注新聞與新聞業(yè)的歷史變遷;其二,將新聞業(yè)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其三,將新聞與新聞業(yè)視為文化形式與社會(huì)慣例,引入有關(guān)權(quán)力、文化的理論,應(yīng)用社會(huì)科學(xué)的概念與框架展開研究。簡而言之,“變遷”“互動(dòng)”“文化”是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三個(gè)關(guān)鍵詞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
在一篇回應(yīng)約翰·尼祿(JohnNerone)的文章中,舒德森(Schudson,1987),明確地與莫特、埃默里等傳統(tǒng)主流新聞史家劃清界限,認(rèn)為自己與亞歷山大·薩克斯坦、丹·席勒等人更為接近,同屬修正主義者和“新社會(huì)史家”。那么,作為修正主義者的舒德森與埃默里等傳統(tǒng)主流新聞史家有何不同呢?
其一,提出的問題不同。埃默里為代表的傳統(tǒng)主流新聞史家所追問的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新聞人是如何展開持續(xù)的努力,沖破種種內(nèi)外部障礙,贏得信息和觀點(diǎn)的自由流動(dòng),并最終使新聞業(yè)成為服務(wù)于的一種機(jī)制的? 舒德森所追問的則是: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新聞(包括作為文體的新聞與作為慣例的新聞生產(chǎn)方式)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 換句話說,埃默里等人所問的是:新聞業(yè)有著何種光輝的過去? 而舒德森所關(guān)心的則是:新聞人為何如此行事?
其二,解釋的模式不同。埃默里為代表的傳統(tǒng)主流新聞史家通常采用進(jìn)步主義的闡釋模式,以沖突論和進(jìn)步論解釋新聞史,即將美國新聞史看作是人們?yōu)榱藸幦鞑プ杂?在與各種控制力量發(fā)生沖突的過程中不斷進(jìn)步,并最終贏得自由的過程。與前者不同,舒德森則更多地轉(zhuǎn)向了文化的闡釋,反對簡單的經(jīng)濟(jì)技術(shù)決定論,將新聞與新聞業(yè)的變遷與更為廣闊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的變遷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考察,既承認(rèn)外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對新聞和新聞業(yè)的制約,也重視新聞人在歷史進(jìn)程中的主觀能動(dòng)性。
有必要對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取徑做出進(jìn)一步追問:為什么他會(huì)選取這樣的研究路徑? 對于這個(gè)問題,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gè)方面尋找答案:其一,他接受的是社會(huì)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其二,他所處的時(shí)代發(fā)生了重要的史學(xué)變革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
在《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舒德森,2009,pp.2-3)一書的中文版自序中,舒德森自我表白道:“我所受的是社會(huì)學(xué)的教育,驅(qū)使我寫作《發(fā)掘新聞》的那些設(shè)想和問題,也都是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 單就本書的立場來看,其社會(huì)學(xué)的框架隱現(xiàn)于背景之中。”眾所周知,舒德森拿的是芝加哥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博士學(xué)位,接受的是社會(huì)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其實(shí),不單是《發(fā)掘新聞:美國報(bào)業(yè)的社會(huì)史》,他所有新聞史研究作品都呈現(xiàn)出社會(huì)學(xué)的底色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不過,盡管舒德森表明了自己的社會(huì)學(xué)取向,卻并未闡明其所謂的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問題與框架到底是什么? 對于此,我們有必要做一番分析。
與其他學(xué)科相比,社會(huì)學(xué)有著獨(dú)特的問題意識和分析框架,《社會(huì)學(xué)之思》(鮑曼、梅,2010,pp.9-11)一書的作者認(rèn)為,社會(huì)學(xué)的特質(zhì)在于:其一,與常識保持持續(xù)密切的對話,省察被視為想當(dāng)然的東西,對于社會(huì)生活中的例行常規(guī)發(fā)問,從而去熟悉化;其二,采用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的分析視角,在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和歷史情境中,對人類行為展開考察。研讀舒德森的新聞史論著,上述兩方面的特征體現(xiàn)得非常突出。
如前文所述,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而且其所發(fā)問的對象正是新聞業(yè)的例行常規(guī),包括客觀性、新聞采訪、概述式導(dǎo)語等。記者遵循客觀性準(zhǔn)則,通過新聞采訪獲取素材,以概述式導(dǎo)語和倒金字塔結(jié)構(gòu)寫作消息,凡此種種,都是現(xiàn)代記者的例行工作方式,人盡皆知,且看似天經(jīng)地義,然而,舒德森就從這些方面下手,并且告訴我們,這些看似天經(jīng)地義的東西其實(shí)并非從來就有的,也不是到處一樣,它們有著自己的產(chǎn)生發(fā)展的歷史,在不同時(shí)空中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在對新聞和新聞業(yè)的變遷展開分析時(shí),舒德森則處處將其置入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時(shí)空,在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的視野中進(jìn)行考察,探討社會(huì)的報(bào)刊與報(bào)刊的社會(huì)。如前文所提及的三個(gè)案例,概述式導(dǎo)語既是美國現(xiàn)實(shí)變化的產(chǎn)物,同時(shí)也成為敘事形式的美國的一部分;采訪的興起與制度化有賴于美國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同時(shí),其本身也是美國現(xiàn)代化的一部分;客觀性既是美國市場社會(huì)的產(chǎn)物,也是美國市場社會(huì)的一個(gè)重要特征。
Barnhurst和Nerone(2009)認(rèn)為,1970年代,美國史學(xué)研究中的社會(huì)史運(yùn)動(dòng)對新聞史研究產(chǎn)生了影響。盡管在史家實(shí)踐中,社會(huì)史以不同的面目出現(xiàn),但也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反對以事件為中心的歷史、反對精英人物的歷史,主張自下而上的視角。這股社會(huì)史的潮流滲透到新聞史研究中,典型地體現(xiàn)在Robert Darnton公文有哪些文體、William Gilmore-Lehne和舒德森三人的論著中。Barnhurst和Nerone指出了舒德森等人的社會(huì)史取向,但對于社會(huì)史本身卻并未展開論述。為了更清楚地呈現(xiàn)舒德森論著的歷史取徑,有必要作進(jìn)一步的分析。社會(huì)史本身有著復(fù)雜的面貌,有一個(gè)產(chǎn)生、發(fā)展的過程,至今仍在演變之中。俞金堯(2011)對社會(huì)史的流變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認(rèn)為:“起源于新史學(xué)的社會(huì)史學(xué),以書寫人民大眾的歷史為其區(qū)別于其他歷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歷史上的大眾文化,因而具有社會(huì)史學(xué)的屬性。戰(zhàn)后興起的新社會(huì)史秉承了年鑒學(xué)派的總體史追求,它傾向于從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尋找社會(huì)變遷的終極原因,以建立宏大的歷史敘事。然而,新社會(huì)史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決定論的弊病,引發(fā)了社會(huì)史學(xué)的‘文化/語言轉(zhuǎn)向’,從而催生了新文化史公文有哪些文體。但是,新文化史強(qiáng)調(diào)文化、符號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話語的首要性,最終走向文化/語言決定論的另一個(gè)極端。對新文化史激進(jìn)傾向的強(qiáng)烈不滿,使得西方史學(xué)界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之后出現(xiàn)了‘超越文化轉(zhuǎn)向’的趨勢,這種趨勢體現(xiàn)在學(xué)者們越發(fā)重視實(shí)踐的作用,社會(huì)史學(xué)正在進(jìn)行一種可稱為‘實(shí)踐的歷史’的新探索。”可見,社會(huì)史學(xué)起源于新史學(xué),經(jīng)歷了從“新社會(huì)史—新文化史—實(shí)踐的歷史”的演變過程。
歐美主流史學(xué)研究中所出現(xiàn)的由新社會(huì)史向新文化史的轉(zhuǎn)變,或者說歷史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起于20世紀(jì)70年代。與此同時(shí),美國的新聞史研究也開始了文化取徑的探討,出現(xiàn)了文化轉(zhuǎn)向。后者與前者的同步,應(yīng)該并非偶然。1974年,詹姆斯·凱瑞(Carey,1974)在《新聞史》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新聞史的問題》一文,批評當(dāng)時(shí)的美國新聞史研究處于尷尬之中,認(rèn)為傳統(tǒng)新聞史研究陷入了進(jìn)步主義的泥沼,提出新聞史是一種文化史,應(yīng)該呼喚文化史的新視角,研究過去的意識,揭示一種文化意識是如何在新聞采集和報(bào)道、新聞組織形式以及對權(quán)力和自由的定義過程當(dāng)中成為一種體制。凱瑞的文章在美國新聞史學(xué)界產(chǎn)生巨大的反響,引發(fā)了美國新聞史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馮悅,2010),包括舒德森在內(nèi)的眾多研究者們自此以后致力于重新界定這一領(lǐng)域,將新聞史中的問題置入復(fù)雜的情境中,以更嚴(yán)謹(jǐn)?shù)姆椒ㄕ归_考察(Folkerts,1991),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綜上,自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主流歷史研究和新聞史研究中同時(shí)出現(xiàn)的文化轉(zhuǎn)向,對舒德森共同產(chǎn)生了影響,使其研究呈現(xiàn)出鮮明的新文化史特質(zhì)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舒德森做的是社會(huì)史研究,倒不如說是文化史研究。
回到本文開頭,國內(nèi)新聞史學(xué)界通過討論達(dá)成兩個(gè)重要共識:一是強(qiáng)調(diào)研究者應(yīng)樹立“本體意識”,確立新聞業(yè)自身在新聞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書寫“報(bào)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bào)刊”;二是主張研究者應(yīng)具備“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擺脫“編年史”的思維定式,尋找史料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從而使新聞史獲得鮮活的生命力文體學(xué)的定義。那么,在操作層面,研究者應(yīng)該具備怎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 又如何確立新聞業(yè)自身的主體地位? 在這兩個(gè)方面,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均可提供重要的啟示。
首先,舒德森從獨(dú)特的社會(huì)學(xué)視角提出問題,并綜合采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理論分析問題。舒德森從兩個(gè)層面打開新聞,一是將新聞視為一種文體(或更為準(zhǔn)確地說是一組文體),二是將新聞視為一項(xiàng)職業(yè)(或者說行業(yè),有一系列的采訪、寫作、報(bào)道的制度和慣例),進(jìn)而提出問題:“作為文體的新聞與作為行業(yè)的新聞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 經(jīng)歷了一個(gè)怎樣的產(chǎn)生、發(fā)展與變化的過程?與其所處時(shí)代的、經(jīng)濟(jì)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文化、社會(huì)諸因素構(gòu)成何種互動(dòng)關(guān)系?”在具體的研究實(shí)踐中,則重點(diǎn)應(yīng)用與文化、權(quán)力相關(guān)的理論展開分析。
其次,舒德森所提出的問題屬于新聞學(xué)本體層面的問題,聚焦的是新聞與新聞業(yè)自身的發(fā)展變化,因而書寫的是“報(bào)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bào)刊”。如黃旦(2007)先生所言,是“站在報(bào)刊的立場,以報(bào)刊的變化起伏以及與社會(huì)諸方面的關(guān)系來展示報(bào)刊的歷史,讓報(bào)刊自身說話,說與報(bào)刊自身相關(guān)的話”。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實(shí)現(xiàn)了三個(gè)融通:一是新聞史與媒介史、主流史學(xué)的融通,二是新聞學(xué)內(nèi)部史、論、業(yè)務(wù)的融通,三是史學(xué)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融通。其中,第二個(gè)融通尤其具有啟發(fā)性,可以為新聞業(yè)務(wù)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向,進(jìn)而使其擺脫長期困守于操作層面的狀況,獲得學(xué)理性。
當(dāng)然,也正因?yàn)槭娴律菐е鞔_的問題進(jìn)入新聞史研究,其筆下所呈現(xiàn)出來的也就只能是獨(dú)特視角下的景象,無法呈現(xiàn)新聞史波瀾壯闊的全貌,因而有著內(nèi)在的局限性。
- 標(biāo)簽:說 一種文體
- 編輯:唐明
- 相關(guān)文章
-
四大文體和四大體裁文體分是什么分文體用品目錄七種文體是什么意思
本報(bào)訊 (記者姜妍 實(shí)習(xí)生宋菲)“有木有”、“尼瑪”、“傷不起”等詞語加上滿眼的連續(xù)感嘆號,構(gòu)成了這幾日在微博上流行的咆哮體…
-
文化用品和文體用品文體形式有哪五種文體思維是什么意思
十年間,尺度關(guān)于體裁行業(yè)高質(zhì)量開展的引領(lǐng)感化正成為業(yè)內(nèi)共鳴,行業(yè)尺度體例事情成就斐然…
- 民間文學(xué)體裁記敘文文體知識課文體裁是什么意思
- 文體類包括哪些東西字體下載軟件免費(fèi)字體免費(fèi)
- 文旅局是什么單位文體課如何上?民間文學(xué)體裁
- 古代文體的三大類文章體裁是指什么,文體類包括哪些東西
- 文體工作是干什么的小說文體有哪些2023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