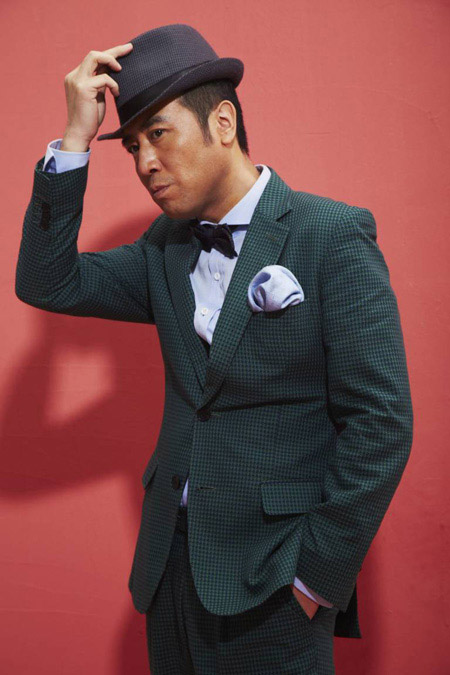共享辦公鼻祖WeWork沖刺IPO:“二房東”仍是主要盈利模式
原標題:共享辦公鼻祖WeWork沖刺IPO:四年累計虧損超40億美元,“二房東”仍是主要盈利模式
前日晚間,共享辦公空間企業WeWork正式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IPO招股書,公司名為“The We Company”,擬議交易代碼為“WE”。
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招股書公開同時也是WeWork(也是行業內)首次有企業公開披露運營數據。從招股書中可以看到,WeWork用了超過7年的時候才讓營收超過10億美元,但自成立開始企業始終處于虧損狀態,且公司自身也無法預測未來能否實現盈利。
作為共享辦公行業的鼻祖,WeWork一直被視為是國內諸多后來者的效仿對象。但作為行業內的頭部明星企業尚且如此,其他玩家苦苦追求的盈利模式,似乎至今仍是一團迷霧。
租金收入仍為主要來源
WeWork招股書顯示,截至2019年6月底,WeWork擁有52.7萬名會員,在全球29個國家的111個城市擁有528個分支機構。其中,52.7萬名會員來自于多個行業,其中38%來自全球財富500強企業。
自成立以來,據招股書披露,WeWork連年虧損。2016年、2017年和2018年,WeWork的營業收入分別為4.36億美元、8.86億美元和18.21億美元,凈利潤分別為-4.3億美元、-9.33億美元和-19.27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WeWork營業收入為15.35億美元,凈虧損9.04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的營業收入為7.64億美元,凈虧損7.23億美元。隨著營收的逐步增大,WeWork的虧損數額似乎也在同步增長。
WeWork在招股書上對此進行了解釋:WeWork累計凈虧損主要來自于門店擴張需要大量的資金。2016年、2017年和2018年,WeWork的門店運營費用分別為4億美元、8億美元和15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WeWork的門店運營費用高達12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的運營費用僅為6億美元。
WeWork還在招股書中表示,短期內其凈虧損占收入的百分比可能會增加,并將繼續絕對增長,WeWork無法預測未來能否實現盈利。
在WeWork的收入結構中,租金收入無疑是最主要的來源之一。截至2019年6月30日,WeWork的固定收益為33億美元,同比增長86%,WeWork預收租金收入為40億美元,約為2017年底WeWork租金收入的8倍。
據披露,目前,WeWork的收入大部分來自美國和英國,WeWork在美國各地的收入大部分來自紐約市、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市場,WeWork在英國的收入大部分來自倫敦。
截至2019年6月30日,WeWork美國的業務貢獻其收入的56%,只有44%的收入來自海外市場,WeWork預計未來幾年將繼續擴大在美國以外市場的業務。
WeWork在招股書中透露,其美國租約的初始期限約為15年。截至2019年6月30日,WeWork在簽署的經營和融資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賃成本支付義務為472億美元,如果WeWork無法履行該項義務,可能對WeWork的業務、聲譽和前景產生不利影響。
WeWork目前在大部分地區簽訂的都是長期租約,除非例外情況,均不包含提前終止條款。根據這些協議,WeWork對房東的義務期限遠遠超過了WeWork與會員的會員協議期限,WeWork的會員可以選擇提前退租,但WeWork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法提前終止租約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招股書中披露,截至2019年6月1日,WeWork的門店中只有30%是成熟門店,其余70%的門店開業時間在24個月以內。(WeWork認為一個門店達到滿租需要24個月,并將已經開業超過24個月的門店定義為成熟門店。)截至2019年6月1日,WeWork的入住率在18個月后穩定在89%左右,并且在24個月后一般保持在該水平。
探索非租金收入以外的渠道
WeWork在上市前最后一輪融資的估值為470億美元,為了支撐這樣的高估值,Wework在上市前沖規模的跡象十分明顯,這家公司用了7年時間達到10億美元的營收規模,接下來用了1年時間達到20億,最近則僅用6個月就達到了30億美元年化營收規模,但短期收入的大幅提升難以遮掩其難以實現盈利的弊病,收入規模的提升是簽下更多長期租約所換來的。
此外,為了支撐高估值,Wework還將自己描述為一家科技公司,并生造出一個space-as-a-service(空間即服務)的概念,但根據其目前的經營模式來看,依然難以擺脫傳統的重資產商業地產租賃這一范疇。
WeWork也在招股書中承認,盡管他們開辟行業先河,但這個行業幾乎沒有準入門檻。為了擺脫“共享辦公”的標簽,WeWork也做出了許多努力:WeWork已經推出了一支名為ARK的投資基金,用于投資房地產;目前已經發展出WeLive共享住宿、WeGrow共享學習等業務。
值得關注的是,WeWork一直在收購互聯網和軟件企業。據Crunchbase,WeWork目前完成了17項收購,包括收購在線活動組織網站Meetup。今年收購的6家公司大多數為業務相關的軟件公司或者互聯網企業。
WeWork在招股書中規劃了公司未來:我們的全球平臺是一站式商店,會員可以訪問他們所需的所有產品和服務,使他們能夠工作、生活和成長。我們已經開始構建一系列We Company產品,并開發第三方合作伙伴網絡以滿足我們會員的需求。
有業內人士指出,共享辦公最基本的掙錢邏輯就是通過服務、創意、運營、差異化等創造出空間的增值,賺取租金的差價。不過這種方式在政府大力補貼的孵化器時期就已經被證實了“壓力山大”。共享平臺集中于一線城市,場地租金過于昂貴,新創企業原本就比較脆弱,如果業主提高租金,勢必將他們驅趕離開。在政策扶持期尚勉強維持生存,一旦失去補貼可能就難以為繼。因此,共享辦公企業不能只依靠“收租”過日子,盈利的模式還需不斷探索。
去年,潘石屹在宣布SOHO 3Q轉型時表示,他最近開始反思包括共享辦公在內的創業熱,很多創業公司拿到融資之后開始燒錢擴張,但賺錢盈利的基本問題都沒有解決。事實上,燒錢快、賺錢慢、營收單一一直被視為共享行業的共同痛點,共享辦公也不例外。克而瑞機構對50家平臺的收入結構監測發現,平均81%的收入來自于工位租金,9%來自于其他租金收入,還有10%屬于非租金收入。
中研普華研究員胡麗認為,在非租金收入方面,投資孵化、社群、撮合成交等都被視為共享辦公的潛力股。然而現實卻各自面臨難點:投資孵化的回報周期較長,環節比較復雜;社群收入存在成員流動性大、共同話題少、變現手段缺乏等問題;撮合成交同樣面臨兩難:若空間不夠聚焦、會員之間關聯性差,撮合成交的可能性就不高;若聚焦到某一細分領域,缺乏行業資源的前提下,入住率又難以保證。因此,共享辦公行業的非租金收入仍然處在探索階段。
但對于如何發展好共享辦公,胡麗表示,在服務方面,共享辦公只有將服務設計緊貼創業者需求,實實在在地提供了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才能贏得了創客們的青睞;在場地選址方面,繁榮的商圈能讓一個企業給大家良好的第一印象,并謀求自身的長遠發展;在人脈資源上,創業團隊的入駐意味著不同領域、不同專業的優秀人才的匯集,這就便利了各個團隊可以通過取長補短的方式尋求合作,從而達到“雙贏”的局面;再看品牌實力,融資熱和行業的調整必定是一番洗牌,規模經濟催促著共享辦公的行業調整。另外,線上與線下,孵化與投資,這個行業升級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 標簽:
- 編輯:李娜
- 相關文章